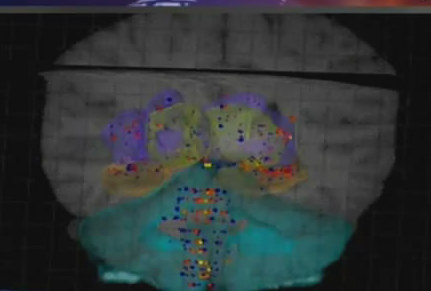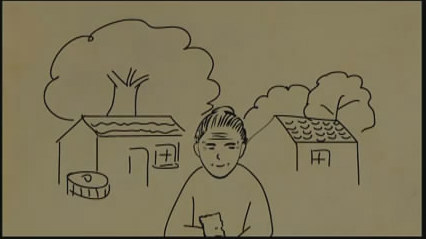“膠面條、皮革奶、石蠟鍋、毛醬油、藥火腿、增稠蜜、糖精棗、氟化茶、鋁饅頭、硫銀耳、箱子餡、甲醇酒、紙腐竹、地溝油……”有人戲稱這張不完全食譜是“中國式菜單”。
常言說,“民以食為天”,可這天大的事卻天天被開玩笑。有人說,這是黑心企業道德淪喪;有人說,這是執法部門監管不力。這些解釋,恐怕都不在點子上,因為這些解釋和對策都忘記或忽視了市場的力量。
梳理起來,食品亂象的特點有“三個多”:一是大企業多,例如三聚氰胺牽涉到的是三鹿、蒙牛,瘦肉精關聯的是雙匯,它們都是巨型企業甚至是行業龍頭;二是生活改善型食品多,銀耳、白酒脫離了基本必需品的范疇,火鍋料、牛肉膏則與下館子有關;三是渠道匿名型銷售多,糖精棗、染色饅頭進的是超市,地溝油、石蠟鍋走的是餐館。
這“三個多”,含義豐富。其中,尤以“大企業多、龍頭企業多”非同尋常。相對于小企業,大企業有規模優勢和效益、龍頭企業更是擁有超額的聲譽租值回報。從私人激勵上看,通過資本市場、上市公司,企業的相關高管也已經與企業的榮辱休戚相關、民營機制下更是身家性命所系。我們不僅要問:“如此這般重重制衡之下,一個大企業、龍頭企業及其主事者為什么竟能夠舍聲譽而不顧、置個人利益于危境、弄虛作假、輕身犯險?”若僅僅以一句“受利益驅使的貪婪”來蓋棺定論,就顯得過于輕飄了。尤其,當這樣的冒險和崩潰不是個別企業的孤例,而是跨市場的群發現象時,恐怕就更值得深思了。
根子在哪里?我認為,根子是居民部門的收入過低。居民部門的收入受限,其凈效果相當于給相應的生產供應部分施加了價格管制。
進一步,強勢的流通環節連續放大和強化了這個管制效果。相對于競爭激烈的生產部門,流通部門擁有強勢地位,它不僅可以將成本變動轉嫁到生產部門消化,甚至可以在鎖定零售價格的同時鎖定自身利潤率,迫使生產部門在零售部門的準價格管制下進行調整。一季復一季、一年復一年,經過若干輪次的反復調整,令生產部門對新的一輪調整和消化越來越接近于極限邊際。
這意味著,對于生產企業而言,這個價格管制的緊縮效應最終強烈到通過常規的工藝優化、成本節省等辦法消化不了的地步,而不得不以降低質量、偷工減料,甚至弄虛作假的方式變形運作。